2024年12月13日,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朱维铮学术讲座,邀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前院长,上海博物馆荣休馆长、朱维铮先生的学生杨志刚教授,作了题为《晚清礼学的若干趋向及特点》的学术演讲,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特聘教授傅杰先生作为与谈人,历史学系邓志峰教授主持本场讲座。

杨志刚讲座现场
一、绪言:晚清礼学相关人物的一组剪影
杨志刚认为晚清是朱维铮先生一直关注的领域,从章太炎、梁启超、《走出中世纪》,到主编《中国近代学术名著·晚清卷》,朱先生的视线没有离开过晚清。此选题是对朱先生的纪念,在其自由而严格的学术精神下谈一些读书体会交流。由此引出对礼在晚清变革的探讨。

朱维铮
礼是中国自周代以来一直延续的政治特色,用礼制来治理国家,隐含着中国文化偏重整体,略有含混的思维方式。在学术视野下,礼是前现代的文化存在,礼学研究分为礼经学、礼仪学、礼论和泛礼学,当下的礼学研究者,多在礼经学的范畴之中,本次讲座也从礼经学的角度切入展开。晚清礼学自1840年到1912年的七十三年间,在自身演化逻辑和内外情势变动的双重力量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异向变动。七十年里比较重要的礼学相关人物数十位,可以分为三列:一是有专门礼学著作者如黄以周、郭嵩焘、孙诒让等,二是经学研究中重视礼学者如阮元、廖平、章太炎等,三是参与甚至主持影响朝廷修礼工作者如曾国藩、张之洞、陈宝琛等。其中一些人的生平跨越清代、民国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在这种跨度中讨论礼学的转型,可以帮助我们从礼学的视角看待近代化的历程。
二、调和、汇通与裂变:学术·政见·伦理
杨志刚引述朱维铮先生对清代统治者为巩固统治而分裂汉文化,引发汉、宋之学对立的角度,将礼学的汉、宋兼采之调和的历史追溯至1810年的国史馆总裁阮元。在此基础上,礼学出现一系列新动向:
将经学归约为礼学,礼学即理学。以礼为理的思潮,是礼学强调实践性的转向。如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所论:“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皮锡瑞《经学通论·三礼通论》所言:“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六经之义,亦以礼为尤重”,以阐发礼对于修身治事的指导意义。
汉、宋兼采,摒弃门户。调和的基调引发对汉宋之学中优点与流弊的理性反思。如郭嵩焘《礼记质疑》质疑郑玄、程朱、陆王;黄式三、黄以周《礼书通故》提出“汉学、宋学之流弊,乖离圣经,尚不合于郑、朱,何论孔、孟?”进而在其主持的南菁书院,“奉郑君、朱子二主为圭臬,令学者各取所长,互补其所短”。杨志刚提出此种反思要放到变化的历史背景中,进而讨论当下我们是在转型的哪一个位置,如何以清末儒生为镜鉴。
实与通接,重提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思潮的兴起是摒弃门户之见的历史结果,譬如“实事求是,惟善是从”(俞樾《礼书通故序》)“实事求是,莫作调人”(黄以周《南菁书院立主议》)等训条。此种思潮推动了学术研究注重辨别援引材料真伪、求同存异的向实趋向,如孙诒让著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等三十多种,学问涉及众多领域,其中《契文举例》为甲骨学开山之作,被章太炎赞誉为“三百年绝等双”。
追溯往昔,会通中西。自晚明徐光启开始倡导“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的中西会通,清末学者再次用礼学的古今融通获取视野闳通和治学方法贯通,进而从诸子之间等传统知识体系的会通,逐渐走向方法论的打通,最后到郭嵩焘、孙诒让提倡的中、西相通,“通合诸科”。

郭嵩焘
调和、会通之风气虽然有勃兴,但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中,礼学很快出现裂变。郭嵩焘参加洋务运动,出任中国历史上第一任驻外公使,他在参观英国海军升旗、鸣炮、奏乐等军礼、学校乐队表演时提出“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认为“三代礼乐,无加于此矣”。由此拓阔了礼学的世界视野,但也被国人骂为“勾通洋人”的“汉奸”。甲午战争的失败促使了礼学裂变的加速,至《辛丑条约》签订后,孙怡让依托《周礼》六官系统,结合从秦汉到晚清的历代治理经验,参照欧、美、日各国新式政治举措,提出革新吏治、裁汰冗官、设立议院、立商部、废科举、兴学堂等一系列具体建议,是晚清礼学家构拟的以近代文明为方向的国家治理方案,表现出礼学解经、辨志、修礼、守道的性格和面貌在晚清裂变为敏感、进击的一面,与传统社会步入近代的面貌同频共振。
三、地域传统的影响与新走向
改革需要具体的精神领袖,而精神领袖又有浓厚的地域色彩。王夫之在晚清受到洋务派的青睐,成为改革的理论武器。1840年,邓显鹤在湘潭主持校刻《船山遗书》,这是王夫之遗著首次大规模发掘和整理。印书不多又遭毁版,流传与影响都有限。1842年,王世全刻船山遗书18种。1865年(同治四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重新汇刊《船山遗书》,共58种。1876年,郭嵩焘在赴英任公使之前上请王夫之入孔庙的疏。在地域传统层面,湖南人选自己人,在推进改革的同时推动地方文化的形成。
他们以王夫之的礼学思想中重祀的特点作为构建其儒学泰斗的依据,如曾国藩《致欧阳兆熊》“王船山先生崇祀之说,忝厕礼官,岂伊不思。惟近例由地方大吏奏请,礼臣特加核准焉。不于部中发端也。而其事又未可遽尔,盖前岁入谢上蔡,今年崇李忠定,若复继之,则恐以数而见轻。且国史儒林之传,昆山顾氏居首,王先生尚作第二人;他日有请顾氏从祀者,则王先生随之矣”。再如郭嵩焘《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臣在籍时,主讲城南书院, 于宋儒张栻祠旁,为夫之建立私祠,率诸生习礼其中,群怀感激奋进之意。东河督臣曾国荃在鄂抚任内汇刻其遗书四百余卷,而所未刻犹多。自朱子讲明道学,其精且博,惟夫之为能恍怫。而湖南自周子敦颐后,从无办过从祀成案……如王夫之之学行精粹,以之从祀两庑,实足以光盛典而式士林”。
历经1877年郭嵩焘和1885年陈宝琛提请被驳回后,借由1907年孔庙祭祀升为大祀为契机,御史赵启霖上《请将国初大儒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从祀文庙折》。当时慈禧太后召张之洞问询,在他的推动下,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进入孔庙从祀。三人的思想曾被清廷视为异说。为了推动走向宪政,洋务派主张使三人进入孔庙,表现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此外,参与地方文化建设还有诸如孙诒让建设学校、黄以周在南菁书院讲学等多种方式。整体而言,虽然湖南人推动王夫之进入孔庙的地方文化建设颇为轰动,但杨志刚认为晚清礼学的“核心”,是江浙的吴语地区,类如“核心肌群”,起到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
四、礼学馆的争议:“制礼作乐”遭遇困局
清廷为建设符合近代工业的上层建筑,相继在六部之下增设部门,相比于工部、兵部,礼部的地位则略显尴尬。1906年,礼部奏请设立礼学馆:“朝廷改良政治,尤以兴学为急务。查户部设立计学馆,兵部设立兵学馆,工部设立艺学馆,皆为讲求实学,立法至善。本部亟应添设礼学馆。”(《议设立礼学馆》)次年,礼学馆成立,但这个礼学馆并非年前礼部设想的用以礼部内部培训、教育的机构,而是由岑春煊直接倡议,并且担负了修订《清通礼》的任务。杨志刚指出,这个转变深有意味,按照中国古代《晋礼》和唐代诸礼的仪制研究传统,自乾隆至道光年间《清通礼》已经修撰完成,而在光绪所处的时代背景下重新修礼,其内涵和背后的政治动机已然发生变化。
彼时礼学馆与宪政编查馆、修订法律馆合称“三馆”,属于清末“筹备新政”的一项举措。在当时同情革命的儒学学者看来,礼学馆的建立是守旧势力的反扑,因此,当清廷邀请当时大儒担任馆长,以孙诒让为代表的很多大儒同情革命,推卸任职礼学馆。这是因为礼学馆的设立使礼学与宪政谁更优先成为争议,直到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以后,清廷才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其第十六条规定“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显示将以民主宪政的原则拟订国家礼制,1911年(宣统三年)六月,礼部降格为典礼院,原职能分解到新成立的学部、民政部等部门。清帝逊位后,礼学馆亦遭裁撤。修订《清通礼》所撰稿本按五礼编排,集为《礼学馆稿本》(残),藏第一历史档案馆(礼部档案)。在这次修礼的过程中,社会各界革新礼俗的要求更趋强烈,在此影响下摄政王载沣谕令礼学馆废除日常君臣之间的跪拜礼,将此载入礼典。此可与郑孝胥《叔孙通》诗所云“节文删跪拜,服色观会通”相映证,但这已无法阻止清廷的衰亡以及传统政治制度的崩溃。
五、近代转型中的晚清礼学
相比于东周秦汉之际,“礼崩乐坏”后所建立起与皇权相经纬的礼乐制度,1840年之后的礼学转型则是在内外因素冲击影响下的第二次崩解。晚清礼乐制度变化的程度比春秋战国更深刻,它要把秦汉以来礼与皇权政治捆绑在一起的错综复杂消化分解掉。这使得民国政府试图借重建“五礼”以重塑皇权和类皇权统治结构的努力不再具有文化根基。
1913年袁世凯准备重建“五礼”,借“礼治”树立威权。康有为提议:“凡新国未制礼,必沿用前王之礼,乃天下之公理也。”1914年7月,北洋政府设立礼制馆,徐世昌任馆长。配合袁世凯祭天的意愿,礼制馆制定《祀天通礼》。发布后激起巨大声浪。袁氏称帝失败后,礼制馆及其编订的礼制被废止。1927年,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下令重新开设礼制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继续推动礼制的编订。1943年国立礼乐馆在重庆开馆,顾毓琇出任馆长。次年,考试院长戴季陶在北碚召集官员、学者开会,讨论修纂“中华民国礼制”,相关文件会后辑印为《北泉议礼录》。戴季陶编撰、出版《学礼录》,序言首句为:“中国为礼教之邦,而礼为吾家先人所独专之事”,表现得相当自得。
杨志刚最后总结:民国频繁的修礼行为恰恰说明制礼作乐的难产,民国的波折证明,“五礼”的时代已经终结,在宪政与法律之下,系统性的“五礼”已经没有时代存在的空间,而当事人,诸如1913年之袁世凯、1927年之张作霖、1928年之南京国民政府恐怕没有此种历史自觉。礼学在近代转型的结局是它撇开政治,回归学术,从孙诒让到周予同,从黄以周到蒋维乔再到杨宽,复旦大学承载了中国古代礼学学脉的一支,并依然不绝如缕地传承、演化、发展、变革,这使得今天我们有机会全面看待礼学在近代转型中的意义。
在讲座与谈环节,傅杰认为,杨志刚教授既在礼学的具体关节问题下扎实功夫,又有宽阔的眼界,呈现出历史动荡中政治与学术的互动。如同周予同先生“真孔子、假孔子”,朱维铮先生“历史的孔子”“孔子的历史”的讨论,都是破经学之为信念、执念的意识。经学是古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礼是经学的中心和社会治理的礼据。礼的很多观念,一直到宪政治国、礼制治国都在讨论。清末礼学馆的建立表现了晚清统治者对西方冲突下中国文化被彻底消解的担忧,并尝试让中国传统与西方宪政在当时并行的逆历史潮流的努力。研究中国文化,经学不可能不讲,这与政治无关。北京学生多受政治裹挟,不如江南学生专心学术,这也使得东南成为经学的传承地,特别是复旦历史系的经学传统延续至今,我们应回顾传统,勉励后一辈继承,以更大的热情和干劲去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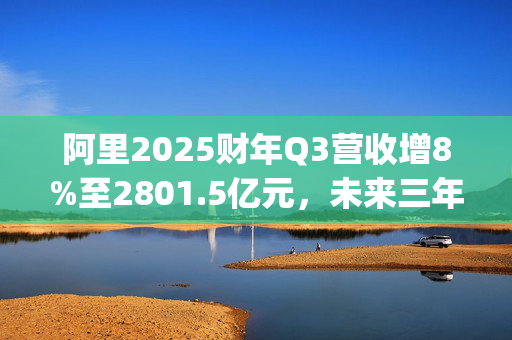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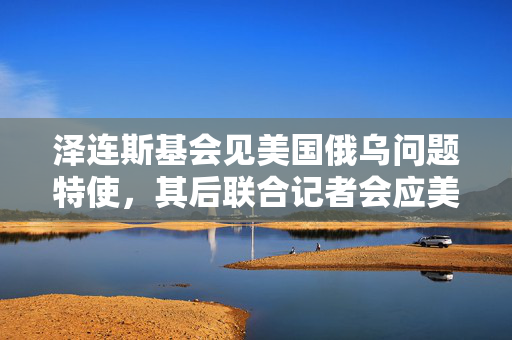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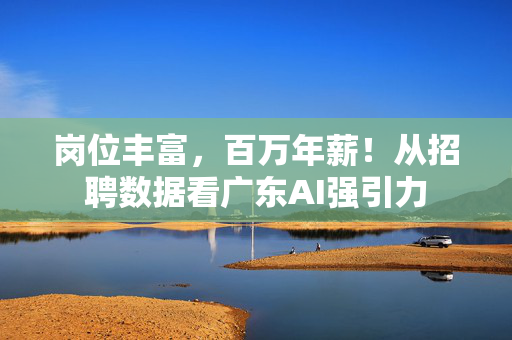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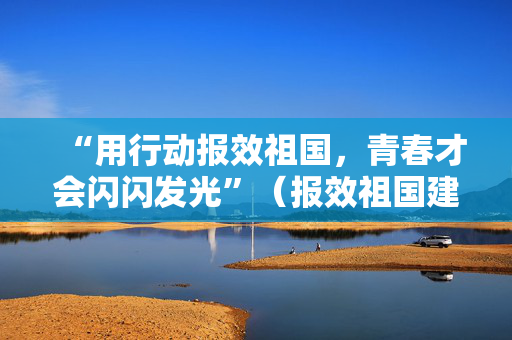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