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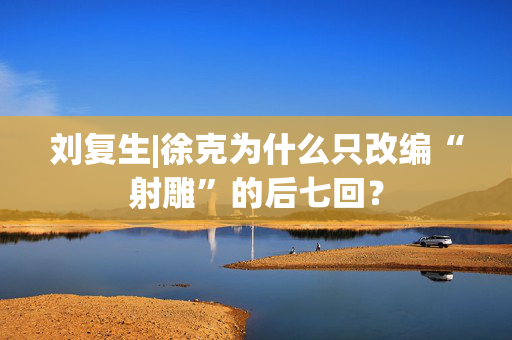
《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以下简称《射雕》),徐克为什么只改了原著的最后七回?很简单,要挣钱,必须这么改。
制片方是这么认为的。
这几年电影业形成一种不好的倾向,重宣发,轻品质。电影成了月饼,点心的属性消失了,过度包装,只管卖相好,月饼票还能回收,成了金融产品。月饼是否好吃,似乎没人关心了。
这种制片路线,极大影响了市场生态,反正电影业无售后服务,也没有索赔机制。
《射雕》是“粉丝向”电影,是这种畸形制片路线的顶峰,当然,也是末路。“偶像”再顶流,再有号召力,如果电影本身品质不过硬,也不可能成功。路人盘不是那么容易被裹挟的。
用粉丝引流,由来已久,是电影业常态,各时代都行,无可厚非。但是,别过分。应该说,几年前也还在可接受范围之内。程耳用王一博,《无名》水平毕竟在线;即使今年,“蛟龙”也用王俊凯,制作还是认真的。
明显可以看出来,近两年,“粉丝向”电影难以为继,外部挑战严峻,内部也越来越卷了。某些制作方,有了危机感和紧迫感。今年的春节档,大概是最后的时刻了。于是,决定梭哈。
它们选择的战略是,既要,又要,还要。全年龄段,男女通吃。对于各个观众群体,都要制造卖点,至少不要犯忌讳。精打细算,针对性下药,必须赢在起跑线上。制作方的小心思,全是这些技术性算计。“封神”和《射雕》是一样的战略,用老偶像费翔吸引存量粉丝,用魔兽游戏吸引年轻人,再针对女性观众塑造个邓婵玉和华筝,必要时卖卖“腐”。谁都不得罪,谁的胳肢窝都挠一挠。小聪明特多,但在讲故事上,却彻底乱了方寸。观众对《射雕》的普遍观感是,不知道电影要拍啥。
说《射雕》是部“粉丝向”电影,不是说它仅仅依靠肖战粉,而是说它的“粉丝向”思维,它把所有潜在观众当成了粉丝,即为了某种单纯外部因素而去观影的一次性顾客。
在制片方的清单上,“粉丝”囊括所有年龄段。对于年轻观众,主打奇幻。除了单纯看“哥哥”的,年轻人更爱看打MOBA,机械降神,古偶仙侠。
针对中老年观众,主打情怀,老年观众更爱看民族大义,中年观众还残存着对武侠精神的向往。“逐草四方沙漠苍茫”,必须看呀。
金迷和原著粉是个庞大群体,他们主要集中在中老年,这批人的观影快感不在情节,而是如何呈现情节,比如欧阳锋如何发明降落伞?年轻观众其实不在乎武侠,“00后”谁还看金庸?连金剧都不看了。徐克连带着中老年的港片情结,“笑傲江湖黄飞鸿,龙门客栈蜀山传”,但对魔幻的老怪风格,年轻人也不排斥。这也是自带流量。
流量,流量,才是王道啊。
流量战略,开局很好,预售火爆,抛开饭圈的操作,宣发的确很成功,挑起了不同群体的观影欲望。
如果片子质量过关,哪怕及格线以上,票房肯定不会差。但是,这种各方讨好的制作路线,怎么可能讲好故事呢?
要一网打尽,只能改后七回。这是聪明的做法,也是唯一的做法。因为,只有这七回浓缩了三国纷争、民族大义和爱情矛盾,神功已成的靖哥哥也具备了和欧阳锋对轰的能力。
但是,宣传片里暗示的侠肝义胆和民族大义,并没有兑现。片花里挑逗想象的精彩场面和动人情节,正片里也没有出现,比如令人血脉贲张的战争、造型奇崛的武打和荡气回肠的爱情……。
天地良心,徐克真的没有魔改。故事线太乱,不是因为魔改,反倒可能是因为过于拘谨,放不开手脚,原著负担过重。结果吃力不讨好,一味赶进度,靠旁白和闪回给剧情不断打补丁,虽然想尽办法,依然顾此失彼,漏洞百出,网上的吐槽也是强人所难。
说好的只改编后七回,却恨不能把全书讲一遍,为什么要背这个包袱?因为想让各方都满意。结果,各方都没拢住。年轻人,如果不是“哥哥”的死忠粉,根本没爽到。他们并不关心原著,七怪和五绝,都是无效情节,一通PPT快速翻页,也根本看不懂,更记不住,不过,这完全没影响。
而对原著粉来说,匆匆忙忙的前情介绍,走马观花,纯属多余,瞎耽误功夫。由于暴力压缩,伤及原著逻辑,也伤了原著党感情。
两军阵前的“欧阳疯”奥特曼发射激光,老观众接受不了——人家编导也不是给你们看的,另有给老观众专门烹制的传统打戏:黄蓉与华筝的屋顶雌竞。不过,老观众认为这是情节上的魔改,根本不买账。但是,只一段魔兽对战,年轻人也觉得不过瘾,而且,强度也不够。武侠片真的没法再拍了,现在已经是个高魔的世界,卷到不会飞和发导弹都不叫会功夫了。想想从《少林寺》到九十年代徐克再到如今的飞沙走石,武功升级的速度有多快。金庸的宇宙已经太低魔了。谁还看拳拳到肉啊,五十米外的发功就已经决生死了。
《射雕》狂打情怀牌,靠硬糊《铁血丹心》《世间始终你好》BGM拉气氛。但偏偏扶危济困、傲视王侯的侠义精神早已沦落。如今流行的是强者生存的哲学。老观众的昔日情怀注定要落空,因为他们自己也已经不再真的相信了。怀念武侠和金庸,只不过是在怀念那个喜欢武侠的年纪,缅怀那个还相信侠义精神和原始正义的岁月。
徐克也是这个旧时代的一员,他在一种自我撕扯中,自相矛盾地完成了旧时代的告别仪式。
《射雕》和原著最大的悖离,不是情节上的。事实上,人们冲着徐老怪而来,早就暗中期待着他精彩的魔改。当年徐克接手《笑傲江湖》,忠实过原著么?但一曲沧海笑,豪气干云,何等洒脱飘逸。“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皇图霸业谈笑中,不胜人生一场醉。”
在金庸看来,侠站在弱者一边,站在大义一边,超越于利害计算之上。固然,原著的写作语境,投射着港英统治下的民族情结,但是,真正界定“侠之大者”的核心,仍是以天下苍生为念的仁爱之心。可是,在如今某些电影人看来,历史的逻辑不过是赢者通吃,胜者为王,这才是他们认为的、观众内心里认同的逻辑,也是观影快感的意识形态前提。这种商业性的法则,和“侠之大者”恰恰背道而驰。
《射雕》尽管还要讲侠义的故事,却已经没有真正的侠义立场。表面看,郭靖坚持无条件的民族认同,站在弱宋一方。但事实上,谁都看得出来,徐克站在大汗一边。所有人都知道,大汗才是最终的胜利者,而且最后成了正统。故事中真正的敌人是金。
为了突显大汗的正当性,故事一再表现宋军的腐败无能,同时不吝笔墨正面展示蒙军的威猛——后来它灭了强大的金,重振了宋衰微的武德。金成了唯一的反派,虽然并未正面出场,它的人格代表是欧阳锋。别忘了,他可是大金的国师。郭靖出手打败西毒,其实是抗金,从而维护了宋蒙联盟。
这和原著完全不同,从“射雕”到“神雕”,宋的主要敌人是元,金从来不是重点。这是延续了民国以来的情感立场。
小说中郭靖与铁木真的英雄之辩,植根于国族立场,却并不限于国族立场,它推己及人,升华到天下的高度。西征的经历,搅起了郭靖灵魂深处的激荡。关于撒麻尔罕之战,电影未予表现,种种顾虑可以理解,但主要原因还是怕有伤大汗铁骑的形象,有损它的历史正当性光辉。不过,这种远征的勇武,不表现未免可惜,于是放在了字幕后的彩蛋环节。
最后,让我们重温小说原著吧,西征途中所见苦难,是郭靖蜕变为大侠的关键。在西域被屠戮的百姓身上,他看到了大宋百姓的命运,也联想起母亲讲述的靖康之难,那也是小说开头,牛家村外,由说书人讲述的战乱中的人生:“几处败垣围故井,向来一一是人家。”
小说的结尾,和开篇遥遥呼应,再次强调真正的侠义主题。郭靖、黄蓉愿望达成,驱马南归。与电影中的happy ending不同,小说中的他们是心情沉重:
“两人一路上但见骷髅白骨散处长草之间,不禁感慨不已,心想两人鸳盟虽谐,可称无憾,但世人苦难方深,不知何日方得太平。正是:兵火有余烬,贫村才数家。无人争晓渡,残月下寒沙!”
(刘复生,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海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海南省文联副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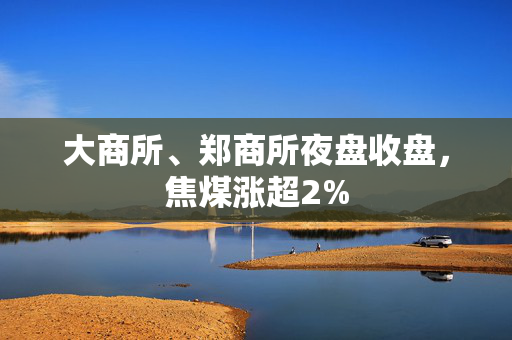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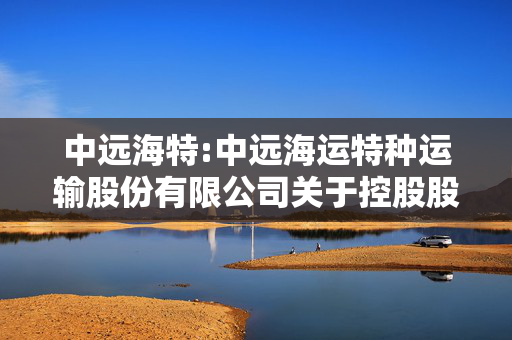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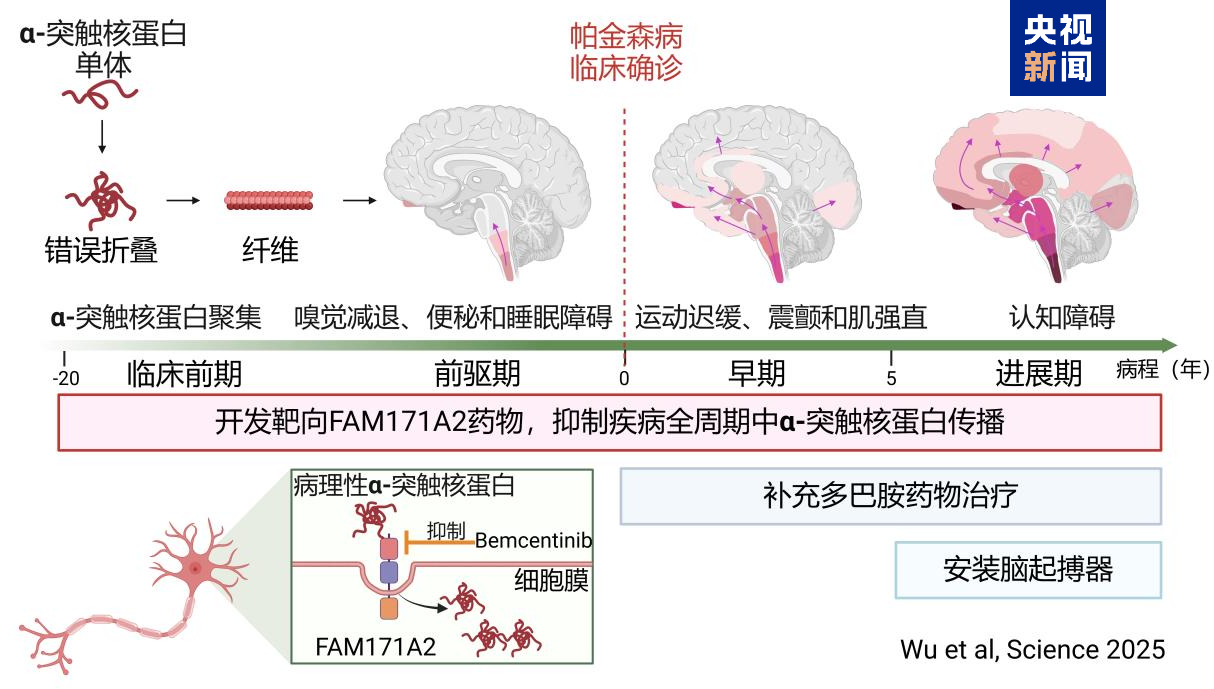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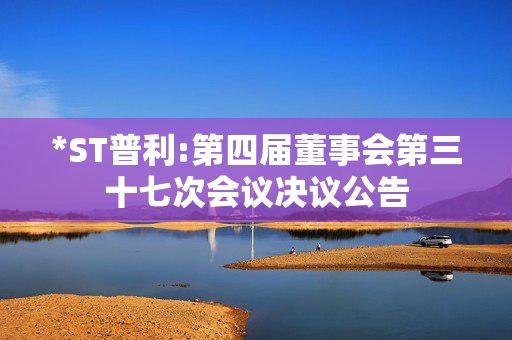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