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想到孔子,往往不由自主把他和峨冠博带、文质彬彬的书生联系在一起,这一方面与大众对他的政治哲学思想中一些观念的典型误解,比如“以德报怨”有关。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常见的“基于现实的历史想象”,即人们总是根据离自己最熟悉、印象最深刻的形象模板,去想象所有同类型的历史形象,最典型的莫过于后世画家为神话时代黄帝、炎帝等部落联盟的领袖绘像时,本能地把他们画成头佩服冠冕的皇帝形象,这当然也是一种刻板印象。
那么,孔子在历史上的真实形象究竟是什么样的,他真的有类似“以德报怨”这样基督教式的是非观和暴力观念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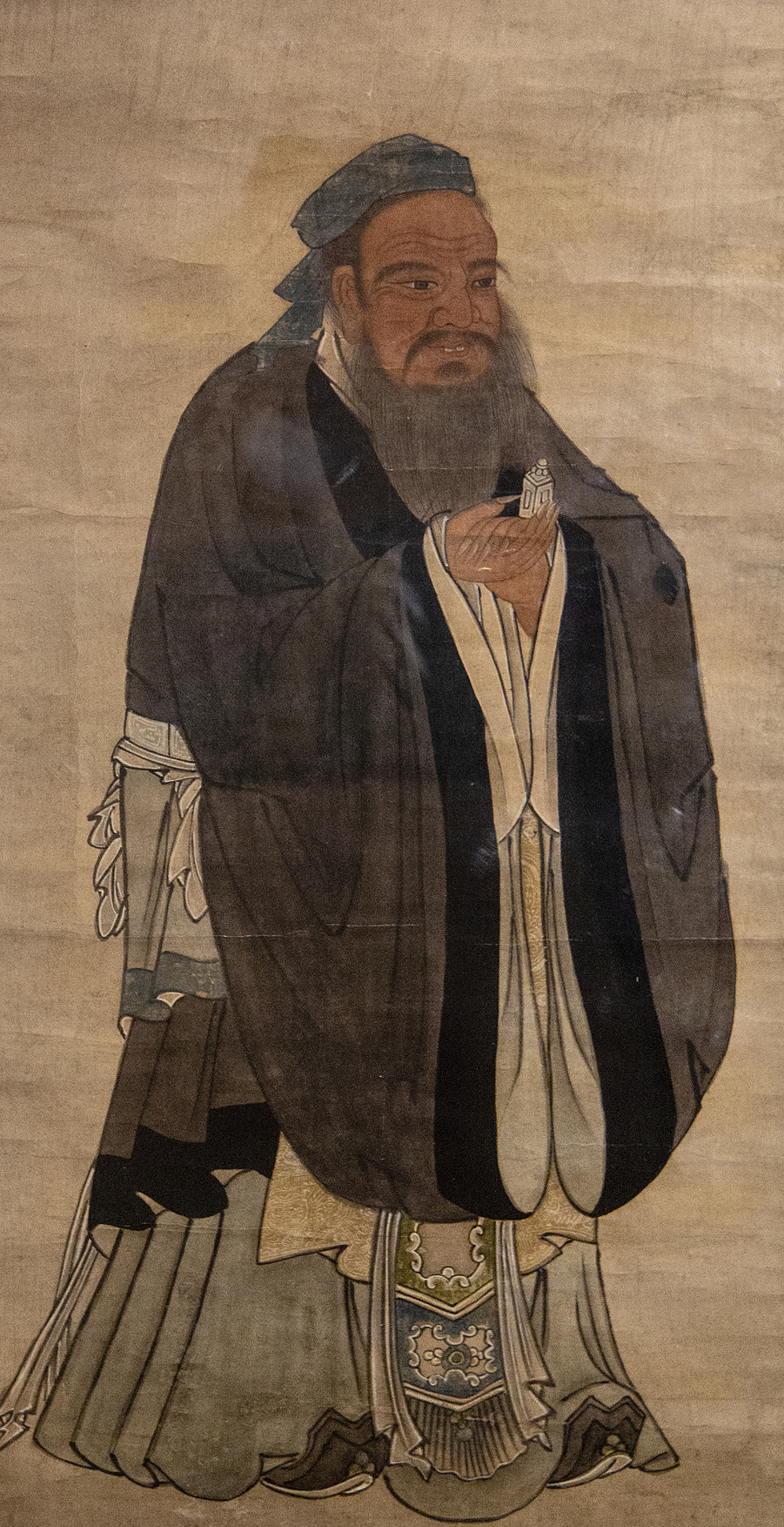
孔子行教像
名将之后
孔子是殷商后裔,武王伐纣建立周王朝后,纣王的两个哥哥投降,受封到宋国。孔子的祖先在宋国经历了一系列政治风波和磨难,落难到了鲁国,身份从诸侯跌落到卿大夫,又从卿大夫跌落到士,到了士这一级。孔子的父亲叫纥,字叔梁,叔梁纥以士的身份作为家臣,担任过郰邑大夫的官职(这是一个官职,并不是说他升级成了世袭的大夫)。但让他在孔子之前就扬名列国的,既不是他“祖上阔过”的出身,也不是他治理地方的政绩,而是他近乎传奇的力量和武功。
《孔子家语》里说叔梁纥身高十尺,因为当时的度量衡比较混乱,按不同的标准,合现在的2-2.2米左右,这在春秋时代算得上巨人了。
在前现代社会,拥有惊人身高和体格的人经常被当作是某种神迹或奇观加以宗教式的崇拜,“力士崇拜”在古代的各个文明中都普遍的存在着,这种体格异于常人的大力士出现在战场上时,那种“天神下凡”的效果往往能让己方士气大涨的同时,在气势上压对方一头。所以叔梁纥很快成为鲁国名将,与将领狄虒弥、孟氏家臣秦堇父并称“三虎”,参与了当时多次著名的战役。
《左传》中叔梁纥的两次出场,都充满了这种天神下凡的传奇色彩,读来令人神往,一次在襄公十年:
晋荀偃,士匄,请伐偪阳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胜之不武,弗胜为笑。固请,丙寅,围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辇重如役,偪阳人启门,诸侯之士门焉,县门发,郰人纥抉之,以出门者,狄虒弥建大车之轮,而蒙之以甲,以为橹,左执之,右拔戟,以成一队,孟献子曰:《诗》所谓“有力如虎”者也。主人县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绝之,队则又县之,苏而复上者三,主人辞焉,乃退,带其断以徇于军三日。(《左传·襄公十年》)
这一段说诸侯联军攻伐偪阳这个地方,武士们贸然杀入城中后中了偪阳人的埋伏,城上的悬门落了下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叔梁纥举起悬门,和另外两位鲁国猛将一起掩护诸侯的武士们安然撤退。
第二次在襄公十七年:
秋,齐侯伐我北鄙,围桃。高厚围臧纥于防。师自阳关逆臧孙,至于旅松。郰叔纥、臧畴、臧贾帅甲三百,宵犯齐师,送之而复。齐师去之。(《左传·襄公十年》)
齐国攻打鲁国,把臧纥围在防这个地方,鲁国的援军一时杀不进来,叔梁纥和另外两个将领带了三百个甲士杀穿了齐军的防线,把臧纥安全送到鲁国援军的营地,然后又若无其事地杀穿齐军防线,回到城里去了。这种极具勇气和英雄主义气概的行为,是古典时代战争中彰显德性的常见景观,会得到无上的荣耀和交战双方的敬仰,史书对此的记载虽短却充满溢美之词,就不难理解了。
武德昭彰
现代人对先秦“士”的想象,很大程度上受限于近世为八股文所误,手无缚鸡之力又五谷不辨,一生皓首穷经沉溺于科举的读书人形象。然而“士”作为封建制度的最低一级,一开始就和欧洲历史上的骑士、日本历史上的武士一样,是和封土紧密结合的军事贵族,其主要的生存方式就是向上级封建主租售暴力,以及提供一切与之相关的军事服务。中国的“士”自觉不自觉的“文武分家”,逐渐失去其暴力属性,是“周秦之变”后很长一个周期内的事。
因此孔子作为一个生活在春秋时代的“士”,军事技能对他来说是必备的谋生本领。得益于叔梁纥的优良基因,孔子身高“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而且《吕氏春秋》里说“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国门之关”就是城门的门闩,一般是一根方形的巨大重木。
九尺六寸约合今1.96-2.05米,这个身高虽然不及他的父亲叔梁纥,举起城门闩的力量似乎也不及他父亲抗住下落悬门那般传奇,但是在贵族也普遍只有1.6-1.7米的春秋时代,孔子这种惊人的体格和力量也无怪旁人把他称之为“长人”,并施以前文提到的那种天神下凡式的崇拜了。
在当时,作为军事贵族“士”要掌握六项基本的技能,即礼、乐、射、御、书、数,又被称之为君子六艺。礼、乐都和祭祀有关,古典时代的贵族战争主要形式就是由贵族驾车互相冲击,按照军事礼仪交战,因此射(箭)和御(驾车)是两项直接的战争技能。而书就是写字,数就是算术。君子六艺看起来只有两项和战争有关,实际上全都是与战争有关的技能,一场古典时代的战争,通常都是从祭祀(礼、乐)开始,以记录(书、数)而结束的。
孔子非常擅长射箭,因此《论语》中充斥着大量关于射箭的内容,以及与射箭相关的比喻。在射箭这项技能中,拉锯是决定弓箭威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同样磅数的弓和箭,射手的拉锯越大,则箭矢的射程越远,威力越大。拉锯与射手的身高臂展密切相关,而被称为“长人”的孔子显然在这项技能上拥有难以比拟的先天优势。而在《论语·子罕》中孔子说:
“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在古典时代的贵族战争中,射手居左,御手居中,戟士卫右,孔子选择做御手,可见他驾车的本领,可能还在射箭之上。
关于孔子的射术,《礼记·射义》里说:
“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
在当时,所有的贵族和“国人”都有军事义务,具备一定的军事技能,射箭能引来人像墙一样围观,可见孔子箭术之高超。但孔子对射箭的态度,又不完全是将其纯粹视为杀伐的手段,而是作为修养德性的途径,《论语·八佾》里说: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可见,孔子将射箭视为一种通过公平公正、互相尊重的“君子之争”修炼精神品格的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武德”是一个一体的概念,首先在军事竞技中体现出高超的技艺,然后才能以强者的姿态展现高尚的品德,如果本身武艺不精贻笑大方,那么武德也就无从提起。如今社会上一些武术练习者或学艺不精,或误入歧途,在擂台上丑态百出,反而在惨败之后大谈武德,试图以此冲淡和掩盖自身的耻辱,殊不知此正是自取其辱之道,武德一体,既然没武,哪来的德呢?
同样是在《论语·八佾》中,孔子又说:
“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他说,射箭不必一定要贯穿皮质的箭靶,因为人的力量天生有强弱的差别,这是古时候就有的道理。前文已经提到,在射箭中决定箭矢威力的因素主要是射手的膂力和拉锯,以孔子的体格和力量说出这番话,很显然是强者在竞技中以上位者的姿态在展现武德。这种武德一体,有武才有德的力量观贯穿了孔子的思想,并被他用于自己的政治生涯,以及之后的教育事业中。
临危不乱
孔子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政治日渐混乱,社会逐渐失序的时代,旧秩序正在崩塌,新秩序尚未建立,共识已开始消亡,底线却不断被突破,用孔子的话说,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所以孔子有这样的体格、力量和技艺,却不愿意像他的父亲叔梁纥一样当一个武将。因为在这样的乱世里,混乱是阶梯,大小诸侯们争抢着拾阶而上,而黎民百姓的痛苦和死亡就是阶梯本身。拾阶者同向内卷,手段都大同小异,对旧秩序稍有怀恋之情者都被时代车轮无情碾过而淘汰,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残酷。在这种情况下,为哪一个“拾阶者”服务的区别都不大,无非是用自身的暴力为这时代的混乱添一把火罢了。
孔子要改变这个时代,最先想到的是获得权力,在他五十一岁的时候,当上了鲁国的大司寇,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职位,虽然孔子未能在这个位置上实现政治抱负,但其间发生了一件大事,却体现了孔子的武力,以及他对武力的理念。
定公十年,齐景公约鲁定公在夹谷会盟。长期以来,晋国的策略是利用鲁国来牵制齐国,而鲁国的策略是依靠晋国来对抗齐国而存活,但此时齐强而晋弱,因此齐国试图逼鲁国改换门庭。这是一个很凶险的场合,夹谷在齐国,齐国如果不能如愿的话可能会暴力挟持鲁定公,而鲁国却无力作出对等的报复和反击,因此鲁国把持政权的三桓都不愿出面,于是让根基不深但职位不低的孔子担任了会盟的相(司仪)。
鲁定公怯懦,担心带兵进入齐境会盟会激怒齐国,给齐景公留下寻衅的把柄,但孔子坚持定公带着护卫部队前去会盟,这一决定在这次历史性事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关于这次会盟,《史记》是这么记载的:
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会齐侯夹谷,为坛位,土阶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旍、旄、羽、袚、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
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鲁君,为之奈何?”有司进对曰:“君子有过则谢以质,小人有过则谢以文。君若悼之,则谢以质。”于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
齐景公先是用东夷的降虏“莱人”在鲁定公面前舞刀弄枪,恐吓定公,被孔子斥退。然后又弄来一堆侏儒来唱歌跳舞戏弄鲁定公,结果被孔子痛斥之后,将侏儒大卸八块,可谓杀伐果断。如果不是身边有孔子这个巨人构成严重的人身威胁,台下有鲁国的护卫部队随时准备拼死一搏,心高气傲的齐景公是绝对不会忍下这口气的,但是孔子确实在胆略和道义上都占据了优势,因此齐鲁会盟成功,且齐国归还了过去侵占鲁国的领土。刨去司马迁因个人情感因素对孔子的传奇化描写,在当时齐强鲁弱,鲁国后继无援的情况下,双方达成了这样一个相对平等的外交结果,对鲁国来说确实是巨大的胜利了。而这一事件也体现了孔子本人的武力水平,以及他对暴力的认识和观念。
言传身教
今人常用“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来批判古代官僚和贵族的司法特权,实际上“礼”是贵族的行为范式,而“刑”是平民的行为范式,这句话本意说的是贵族和平民的行为范式不同,结果后世曲解成破坏法的同一性原则,是典型以今推古的谬解。孔子就主张打破血缘藩篱,让平民接受博雅教育,按照小贵族“士”的行为范式生活,这样就大大扩大了“士”的规模,使从前“非人”的群体获得民权,构建以士为基础的古典公民社会,即大同。因此孔子在教育中,也很注重以文武双全的士道标准来要求弟子。
在孔子的弟子中,子路是最为特别的一个,在《论语》中,子路分别以不同的称呼出现了77次,远远高于其他所有弟子的出场频率,可见其地位之高。但是在这77次“出场”中,大都是师徒二人的思想和言语交锋,可见孔子对子路批评之切。实际上,孔子对子路的教育过程,比较完整的体现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武德观。
子路名叫仲由,字子路。《尸子》里说他是“卞之野人也”,在西周时期,被称为“国人”的武装殖民者住在城邦“国”之中,既享有古典公民的一切政治权利,又承担诸如筑城、作战一类的军事义务。而住在城邦之外的平民被称为“野人”,既无政治权利,也不承担军事义务。子路就是这样一个本该一生都与“文武双全”无缘的“野人”,但此时的社会处于剧变期,争霸战争正在向着兼并战争转化,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平民开始大规模参与战争的结果之一,是最低级的军事贵族“士”和平民的界限开始模糊,有士下落进入平民,也有平民上升进入“士”这个阶层。
子路就是这样一个出身平民,但是又在行为和做派上具有某些“士”的特征的人。他少年家贫,但又非常尚武,经济状况改善之后,他自恃勇力,行事风格十分高调。孔子讲学时,子路前去捣乱,二人初见时,子路“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子路的冠上装饰着雄性雉鸡的长尾,身上佩戴着公野猪的獠牙做的觿,想找茬把孔子打一顿。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形象,雄性雉鸡的尾翎自古就是武将的象征,商周时期的青铜头盔的盔顶上就有专门插雉鸡尾翎的插管,至今仍能在京剧中看到这种头饰。觿是一种用动物的獠牙制作的工具,可以用来解开绳结,在先秦时期和射箭用的韘成对出现,《诗经》有云“芄兰之支,童子佩觿……芄兰之叶,童子佩韘”,先秦时代的人认为,觿和韘这一对器物象征着士智勇双全的理想人格,在遇到问题时,既要有用觿(文)去剖析谜团,解开乱局的能力,也要有用韘(武)杀伐决断的能力。
可以说,子路这时的心态,和黑泽明的名作《七武士》里假扮武士的农民菊千代非常相似,他虽然没有士的出身,却在装束上尽量去贴近他想象中“士”的外形,他尚未具备士的修养和德性,却又拥有了士的武力,他既鄙视已经没落的士,又渴望得到他们的认可。《孔子家语·好生》篇说:“子路戎服见于孔子,拔剑而舞之,曰:古之君子,以剑自卫乎?”子路拔出长剑来在孔子面前挥舞以炫耀武力,质问他,他所推崇的那种古代的君子,会不会用剑自卫呢?这显然是子路作为一个唯暴力论者,针对孔子的政治主张提出的挑衅,子路的思想在当时很有代表性,就是世道已经坏了,你们这些腐儒讲这些大道理有什么用呢,这世道唯一好使的就是拳头,我就信这个,所以他打算“陵暴孔子”,从肉体上战胜孔子的思想,来证明孔子的无用。
子路是如何从“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突然就“儒服委质,请为弟子”的?史书上对这一戏剧性的“踢馆”过程语焉不详,后世有大儒认为,孔子是用道理折服了子路。这个解释很牵强,从子路的角度来讲,他来寻衅的根本原因就是认为孔子的道理无用,一个坚信道理无用的唯暴力论者,专门前来证明道理无用,又怎么会被道理折服呢?
从孔子的观念来说,君子能不能用暴力?当然可以,君子要掌握比一般人更高的暴力。但是君子不能二话不说上来就用暴力,要先跟对方讲道理,对方不讲理怎么办,当然是用对方能理解的方式去交流,交流之后不能一走了之,还是要讲道理,这时候对方就比较容易听进去了。物理和道理手段都用上了之后,仍然冥顽不灵的,这时候消灭他也是符合王道的,这就是论语里说的:
“不教而诛之,谓之虐,教而不化,诛之,谓之王道《论语·尧曰》。”
孔子是不是用子路理解且信服的那种方式说服了他,如今已不可考,但子路拜入孔子门下后,很快就和孔子讨论了关于自己曾经信奉的“唯暴力论”的问题,《论语·阳货》里有一段对话: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子路问“君子难道不崇尚勇武吗?”,孔子回答说:“君子的价值观重,义才是第一位的,君子有勇而无义,就会变成祸乱朝政的国贼,小人有勇无义,就会成为祸害平民的盗贼。”
可见此时,子路实际上没有完全放弃唯暴力论,仍有些不理解或者说不服气,而孔子指出了他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没有“义”来作为准则,肆无忌惮的暴力只会成为祸国殃民的力量。子路在初遇孔子之前,正是在国贼和盗贼的边缘徘徊。
在《论语》中类似的对话还有很多,子路在这种对话中,多少显得有些桀骜。但他的性格质朴刚健,行为果敢坦荡,不悦就拔剑相向,信服就真心求教,这种优良的秉性使得孔子对他的批评更多的带有爱之深,责之切的意味。
子路的性格,很符合前轴心时代部落武士的特点,所以孔子说“野哉由也”。这和先秦儒家提倡的“诎于言而敏于行”的主张有天然相通之处,因此子路其实是最容易成才的,但这种性格也存在问题,就是容易因急躁而鲁莽,因鲁莽而导致非理性的冲动和行为。同时,很容易对暴力和强权形成路径依赖而无法自拔。孔子对子路的整个教育过程,实际上是在压制和化解他性格中有问题的那一部分,而让他性格中好的那一部分自由生长。
在《论语·先进第十一》中,孔子曾经对几位得意弟子的性格作出一个判词式的总结:
“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论语·先进第十一》)
孔子的诸弟子陪伴在他身边,其中闵子骞显得和悦恭敬;子路则刚强而桀骜;冉有、子贡侃侃而谈。孔子很高兴。然后孔子说:“子路这样的性格,恐怕难得善终啊!”很多人错误地把这句话理解成孔子咒骂子路会死于非命,并把这句话和子路的死亡联系起来,认为孔子“一语成谶”,这实在是典型的望文生义。孔子这样评价子路,是因为他的思想代表着那个时代最主流也最危险的思想倾向,即唯暴力论,孔子说他会死于非命是有语境的,是在教导他滥用暴力者必死于暴力的道理,但子路最终结缨而死,用生命践行了士道,而不是死于滥用暴力的反噬,说明他遵从了孔子的教导,也说明了孔子对他的教育最终获得了成功。
由此可见,对孔子及其弟子非但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酸臭腐儒”,而且在自身掌握着高超军事技能的同时,还对暴力的本质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力量”是儒家思想最核心的理念之一,这一理念贯穿着“仁”“义”等多个核心概念,可以说,不理解孔子的暴力观,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儒家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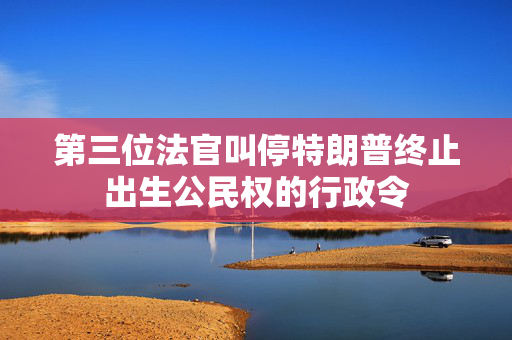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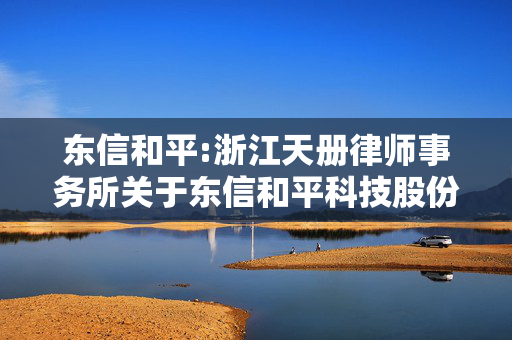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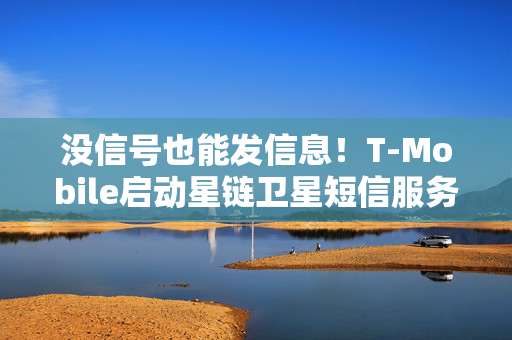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