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标题:月入 800 元的劳务派遣,啃老考公的全职儿女,县城 " 废掉 " 的青年自我如何构建)
经济背景下总体的就业难,就业选择中的不愿意脱离县(市)域,大学学习专业的限制(尤其是文科),中西部县域非考公就业机会有限,家庭经济实力与家人无条件支持,等综合因素诞生了县城里的一批啃老青年,考公青年。今年回家参加同学的婚礼,见到了很多朋友,聊了聊,啃老的考公儿女在老家也很普遍。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边就业边备战来准备考公,如小 A 在县某国企部门作为劳务派遣人员,每个月工资扣除五险外到手八百,直言不够自己一个月烟钱。二是全职考公青年,如小龙,小标等,他们 2020 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备战考公,四五年有过进面机会,但都被刷,每个月家里给他们两千元,小龙的妈妈说自己家里有钱,绝对不允许他半途而废送了外卖,自己愿意养,直到 35 岁不能考了家里才会死心。
和他们深入地交流了一下,发现了普遍污名化下的他们有着自己的应对之道。如何理解自己的过去几年?
一,自己的视角:迷茫的几年
" 不像家庭条件不好的同学,啃老是没有条件的,全职备考也是没有可能的,家里养不住闲人。"
" 全职儿女也好,啃老也罢,家庭条件好的才能有这条件,我们的出身给了好的物质基础,也同时产生了我们废掉的大学生活,那会就顾着玩,没有思考未来做什么,也没有特别的危机感,做事没有目的,毕业后别人考公我考公,但不过是盲从,每次都是临时努力 "
他们将自己的生活总结为回过头来是寻找目标和认识自我的几年。
那么这几年他们经历了什么?
一是封闭自我到拥有被讨厌的勇气。朋友说他们很害怕过年。每次过年的时候,家里的长辈都要问他们什么时候工作,会讨论家庭中后辈中的优秀者,而他们自然是舆论的中心与被批评的中心,在长辈面前又不敢去顶撞也确实很难去改变世俗的观念。所以更多的时候只能自己闷着喝酒,自己把自己灌醉。他们也很害怕同学聚会,每次聚会的时候,看到有的同学一路读书,有的同学已经成家立业,明明都是年龄相仿的曾经的同年级同学,却在人生的道路上相差很远。他们说 倒不是羡慕或者嫉妒,而是觉得自己成了那个异形者,边缘人。
所以刚开始备考的两年 他们将自己封闭起来。认为只要考上了就可以再融入家庭和同学的世界,但多次的考试失败,长时间段的自我封闭,他们也会觉得自己的精神世界出了问题,所以一种人是更加的封闭与走向抑郁,另外一种是建立起被讨厌的勇气,觉得自己只是在努力地探索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并且这种被讨厌的勇气有基础,他们一旦考公成功,就是本地区对成功青年定义的首要标准之达成,过去很多的不理解、不尊重、不认可都可以变为夸奖,荣耀,释放善意。加上考公越来越难,他们身边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啃老全职考公是身边人越来越支持。
二是追求意义到不愿意去思考。他们说。从大学教育或者应试教育来讲,仿佛自己应该每天的生活,每次的行动,都是要有目标和要有意义的。如果这样理解,自己废掉的这些日子就索然无味。这是成功学对个体的定义。一开始他们也不能适应,总感觉自己在一直在堕落,不停地堕落,没有底线的堕落,且堕落没有尽头。时间长了,他们要开始去重新定义自己,定义生活。于是 又有了青年群体的分化,一种是不去思考意义,把自己的时间填满,于是县域的麻将馆,台球厅,网吧,人很多,不仅是低学历的社会混混青年,也有不少全职考公青年,他们要通过在社群里找到自己的同类人,混混是他们不可能建立关系的群体,而同样的考公青年是有共同话题的。第二种是否定意义,建立自己的生活目标,认为生活本就是没有意义的,考上了为人民服务是意义,剩下的所有都是为了钱,为了工作,所以不愿意去思考。小 A 便是如此,曾经觉得自己做的事没有意义,即便劳务派遣工作也没有意义,深夜睡不着。后来他明白了,大多数人都是以过日子为主的,意义太高尚了,不去想,每天也能过去,自己活得反而轻松。
三是多元交际到构建自己的舒适圈。今年回来,发现这几个同学在全职考公的同时都谈起了恋爱,其恋爱对象也多是本地的全职考公女青年,有的是通过报考同样的培训班认识的,有的是朋友介绍的,因为县市区本就不大,通过同学关系、朋友关系都能建立联系。不仅恋爱对象在走向同质,其日常交流的朋友除了同学之外,很多也都是备考青年。这倒也正常,因为都在参加备考,就有共同的话题和信息可以分享、交流。互动频次高的就可能成为朋友。但这些同学也分享自己其实很苦恼,刚毕业的时候朋友很多圈子也很大,因为自己拖沓了几年,曾经的很多朋友工作的工作,升学的升学,没有了共同话题,交流很少了。他们感觉自己困到了一个信息茧房的社会环境中,因为学过结构论,能够用审视的眼光理解自己的处境,一方面 他们很明白自己的世界越来越封闭是正常的,另一方面 他们又为自己这种清醒的痛苦活着而感到绝望。仿佛自己在坠下一个深渊,如果没有上过大学,即便混了几年也不会去思考这些东西。现在就是大学教给自己的知识与自己的成长阶段不匹配,自己没有达到预期生活。小龙说痛苦的清醒还不如麻木地活着,可惜时光不能倒退,如果重来。要么自己不会选择上大学,要么自己会更有目标和计划一些。
二,父母的视角:成长的几年
小龙的父亲是正式的煤矿工人,母亲是高中教师,他的父母认为家庭收入一个月能达到将近 2 万,家里就小龙一个孩子,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让小龙阶层滑落,不愿意让他从事非正式工作。其他几位同学的家庭条件要比小龙还好,小 A 的父母都是体制内有一定地位的干部,小龙的父母在银行工作且父亲是高管。
一是不允许孩子失败到孩子有一份工作。相比于大学还未毕业的时候。父母对他们的高期待,认为他们需要在省城找到一份儿体面的,走出县域实现家庭的跃升。几年下来 父母支持力度不减,但早已没有了当年的高期待,只是希望孩子读书一场 不要最后成为普工。他们也比较想得开,认为自己攒下的钱,与其将来给孩子买车买房,远不如现在给他们投资,让他们啃老,全职备考,再搏一搏,哪怕在县城或者乡镇找到一份事业编工作都可以。不求孩子们能有多大的出息,只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有一点收入,父母就是他们的家庭银行,愿意一直让孩子啃老。唯一要求就是能够有份工作,作为成家的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小 A 说自己一开始在家庭生活中感到绝望与窒息,因为父母不理解自己,总觉得自己考不上是因为不努力,言语中都是 " 刀子 "。直到这两年,父母才回归平常心。他说。正是父母这种逐渐学会克制的理解与爱在包容他,他才不至于感到崩溃。所以,啃老必然要经历与父母和解的过程。
二是从卷孩子到卷自己。对于这些中产的家长来说,衡量自己孩子是否成功的评价元素比较单一,主要就是找到体面工作,实现家庭向上。因为家里有经济实力,所以就愿意做被啃的父母,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他们也在重新去思考孩子的未来,认为孩子需要从全职儿女走向社会,即便是一份儿收入不高的劳务派遣工作,也可以让孩子接触社会的不容易,增强内在的考公驱动力。这样的观点来自他们认为自己把孩子保护得太好,以至于子女没有干劲与拼劲。所以,家长们开始从卷孩子到卷自己,小龙说他的父母这两天开始看教育自己的书籍和视频,并在试图用于家庭教育,他能看到父母在变,因为压力不仅是小龙的,小龙的父母也面临压力,工作成功但育儿不成功,父母也有世俗的烦恼。小标的父母则加强了和亲戚朋友的联系,关注了很多考公培训的公众号和网站,到处搜罗信息,生怕小标错过了可能上岸的机会。小 A 的父母则说 现在开始学习理财和创业,要给他留下更多的家底。
三,从污名化到还原:结构的产物
全职儿女产生于中产家庭,农家子弟没有条件,所以,占多数的青年家庭基础好,家庭期待高,在中西部,这种能满足高期待的工作只能是体制类工作,行政编,事业编,国企员工等,好的岗位稀缺且面临高度竞争,备考多年不上岸实属正常。家庭又有实力,又不愿意孩子从事非正规工作,全职备考的啃老年轻人自然就在家庭诞生了。
从调研和过年回乡接触的青年人来看,家乡偏好与不出省进一步压缩了自己的选择空间。因为在本地有优渥的社会关系,也很熟悉地方社会的规则,人情世故,再加上大学期间就在本省就读,带来了他们不愿意出省的想法。所以 区别于山东的全国巡考,到处找机会,他们更喜欢地方的安逸。从我所在的高中班级来看,高考后在外地上大学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在外地安家立业,在本地上大学的年轻人则很少外出。这一部分人在高考时并没有拔尖儿,加上父母认为在本地就读更有利于家庭支持,所以不愿意出省是高考之后本地就读选择的结果。
对于他们的这种心态的变化,如何产生?可以从家庭和社会两个视角进行理解,值得继续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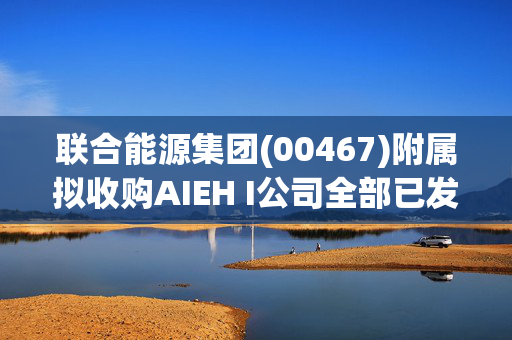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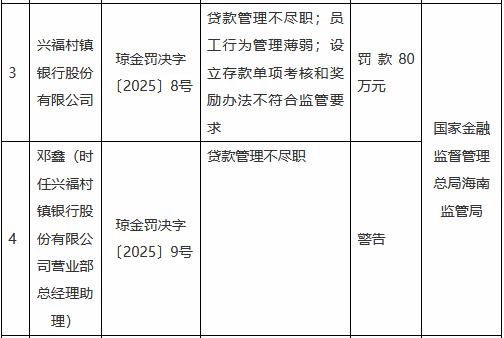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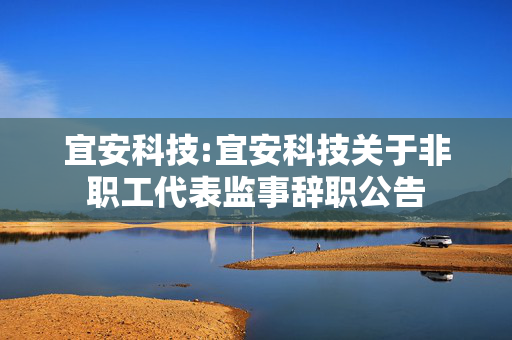



发表评论